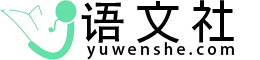与尘土一起走散文
我不知道怎样述说尘土的分量,或许,正因为过于细微,小如芥末,才使它们有了更宽泛的存在空间。生活中的尘土无处不在,谁也拒绝不了。它们没有翅膀,却能借助气流的外在力量,自由地行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任何地方落脚。有时我想,是不是有人曾经在清扫尘土时,享受过这种琐碎劳动所带来的快乐?

尘土的力量似乎是强大的,比如位于西北六盘山地区的它们。西北的风,好像从来没有平静过,一直躲在四季的光影中,在适当的时候,为尘土的行走,起推波助澜作用。这一年的深秋,许多地方下雪了,而六盘山地区却少见雪花飘落,每年按时令光顾的雪,好像传说中的公主,让人充满向往和期盼。通往老家的道路,和高低起伏的山峦一样,曲折蜿蜒。山上已经没有什么绿色了,灰朦朦的,大地枯萎,如同一个人阴暗的心情。山道漫漫,秋风从山顶滚落,打着旋儿,碾过枯草和田野。踩在脚下的路面,不时有尘土扬起,穿过鞋面,透入裤管。背着光线,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细微的粉尘,四下漂浮,到处弥漫。
路上总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要到附近山下的集市上去,购买他们需要的化肥、鞋袜和调料。他们戴着厚厚的帽子,穿着便宜的防寒服,勾着头,背着风,顶着扬尘,行色不紧不慢,样子和路边站立的柳树、杨树、蒿草一样,因布着灰尘而显得灰暗、沉重。偶尔,抬起头互相说笑几句,眼睛发亮,牙齿洁白。从神情上看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高,和风尘对抗似的,但还是会被秋风和扬尘湮灭。偶尔有车辆驶过,尘土随即飞扬了起来,铺天盖地,气势汹汹,行人都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呛鼻的土雾里。可谁也没有停下行进的步伐。远处,就听见有咳嗽声传来,却没有有抱怨和责骂声。
其实,我,我们习惯了与尘土一起生活。六盘山绵延千里,到我们老家时,山峦一改挺拔、苍翠的气势,变得灰暗、低矮了起来,好像试图安心过日子的老人,内敛而且谦逊。但这样的环境并不是平静的。干旱少雨,加上气候温差大,所有的土地都需要雨水霜雪的滋润,包括那些站立多年的柳树、杨树,以及长期生活在崖壁、地埂的荆棘、荒草。许多尘土,就隐藏在植物叶片之下。地面上的浮土,稍有动静,就会借机脱离主体,试图流落他处。我们老家,对沙尘暴这个词语显得十分陌生,就像对一个熟悉的人,突然有了一个拗口的叫法。我们把沙尘暴叫做黄风土雾,雾是尘土形成的,连风也有是土地的颜色,诗意而且色彩斑斓。春秋两季,是黄风土雾多发期,风总能和尘土结伴走在一起,孪生兄弟一般。我一直以为,是树刮起了风,树动风起,风起雾生。村庄四围的山,树木说不上葱郁,但一个紧靠一个好多年,它们摇晃时,村北的山口,就有风涌进村庄,便有尘土搅和在风中,由高而低,甩打而来。窗户、屋瓦,发出动物疾速行走的声响,枯草、树叶、羽毛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纸屑、布片,蝴蝶似的在风尘中舞蹈。麻雀这种生活在村庄的土著,显然不抵风尘的力量,仓皇失措间,往往撞在屋檐下。天空包裹在灰色的麻袋里,日光收藏在风尘中,宛若是一个混沌、原始的世界。或许,大自然正在着手创造着另一个未来。
这种境况大约会持续几分钟,有时几十分钟。风停之后,大地清爽,天空明净得圣洁。隐藏在草叶下的尘土和地面的上浮土,被清理在村庄的某个角落。村庄的人们,脸上挂着胜利般的笑容,好像来到另一个明亮的村庄。只有在这时,才能领会到黄风土雾对一个村庄的重要作用。我的母亲,一位小脚妇女,提着扫帚,清扫院子和院落四周的尘土,不知疲惫,充满快乐。母亲说,土就是土。她把那些尘土收集起来,要不倒进附近的土地里,要不归进牲口圈里。村庄的尘土,是纯粹的尘土,肯定提炼不出金子并做成蔷薇花,但它们一旦融入土地,却能在它们的身体上长成养人的粮食。
甚至,老家的尘土是洁净的。山坡之上,除了种植了成片的树木,其它的大约尽是粮田。土地并不肥沃,适宜于土豆、葫麻、豌豆和小麦的生长,它们都是村庄的财富。六月麦黄,日光炽烈,焦土、绿草、麦香的混合味儿弥漫,纱一样笼罩着村庄。如果没有瞬发的雷阵雨,风和尘土们显得十分安详,似乎在观看着收割忙碌的人群。有时,我也是收割队伍中的一员。卷起的裤脚,赤裸的胳膊,常有麦虻光顾,不知不觉中,某处红肿一片,骚痒难耐。我没有经验,倒是母亲,她在手指上吐一点唾沫,沾上地边的尘土,涂抹在红肿处,几分钟后,红肿渐消,皮肤也不再发痒。尘土的这种功用,的确屡试不爽。母亲说,这不是她的发现,村庄里的人大致都是这样。我惊奇地发现,尘土的用处不仅在于止痒消肿。常和土地打交道的人们,皮肤被青草或者刀具划破皮肉是常有的事,我亲眼所见,一位和我同龄者,手掌不小心被镰刀割破,鲜血流出时,他的父亲,顺手抓起路边的面面土儿(细土),压在了刀口上。血很快止住了。当然,医生肯定是不赞成这样处理伤口的。后来,我知道,只有炎阳烧烤下的尘土,才有清火消毒的作用。后来,又知道,村庄里有人头痛上火时,常用熟土水清火——把土块放在锅里翻炒,待土块的颜色由红转黑时,猛地浇上凉水,“哧——”一声,白色的蒸气和焦土味儿四处弥漫。然后,把这种水沉淀后小口饮用,效果不比药片差。
尘土因为细微,它才长上了飞翔的翅膀,又因为它有重量,却能随地扎根,融入眼下的生活。我曾经在微醉后对一位友人说,我是一粒永远漂浮在路上的尘土。不是吗?一九八六年春天,春风卷着尘土的日子里,父亲带着我离开了村庄,来到了小城谋生活。好多年里,我们父子租住在一间过去的仓库里。仓库临街,可能是为了安全,它的主人把窗户全用木块封了,从木块的缝隙间透进来的光条,将仓库分割得更加灰暗、琐碎。工作之余,我愿意趴在仓库的窗口,把目光展向外面,以此来缓解劳作的疲惫。和老家一样,小城的沙尘暴也会按时光顾,那时,仓库外面混乱而且昏暗。风从街道上的电线上掠过,发出的声音尖利、冗长,甚至让人恐怖。不知从何处而来的纸屑、塑料袋在半空中漂浮,一些扑到树枝上挣扎着,样子滑稽却又似痛苦。含有工业砂砾的尘土,似乎用愤怒的方式甩打玻璃,我担心小城的一些东西过于脆弱而支离破碎。在沙尘暴制造的汹涌海洋里,我敢肯定,其中有几粒是来自于六盘山下老家的尘土。
多年来,我经常游走于小城于老家之间,不分季节,不知疲倦,就像这个秋天。这个秋天,风不断刮起干旱的土地上的尘土,四处传递着老家的消息。老家里,有不少人感冒了,他们在剧烈地咳嗽,将肺要吐出来似的。这与秋风和尘土无关,人们只是期盼有一场雪落下,将尘土归还给大地。我缓慢地走在山道上,枯草、几片还没有凋落的树叶,在眼前晃动,让人觉得生命总是很顽强,又很脆弱。我家的一些土地,小麦已经低下了昂贵的头颅,即将进入冬眠。父亲老了,他再不能带我远走他方。我要在我家的这些土地里,为父亲选择一块安身之地。脚下的土地,不时飞起熟悉的尘土,迷离双眼,染灰头发,还钻进鞋袜,和肌肤相亲。父亲要回到土地,我迟早也是要回去的,毕竟,一粒尘土,最后都要落到大地的怀里,毕竟,我们都是土地的孩子。
【走了多少年】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山村。
不管是从县乡公路还是国道行走,都会抵达目标,一点不会有错。沿国道回山村,是近几年的`事。坐车,或者骑自行车,朝东,驶上靠近小城的东山,进入国道,约二十几分钟后,右拐,与国道分手,爬山,过沟,绕过几个村庄,翻过山崾壑岘,就会和山村撞个满怀。这儿,有好几条道路可供选择,如果时间宽裕,可多绕几座山,多过几个村庄,远看一山绿树,近看盈盈水坝。即便是步行,抛开大路,也有许多山道捷径,徐缓而行,一不留神,山顶之下,就是山村。
对于行走的路线,也是有感情的。比如,我习惯沿县乡公路回家,虽然和国道对照,有些费时,但走了近三十年,总觉得这条路顺畅、平坦。通常,坐班车过甘渭河,步行到店子壑岘,再穿过条沟,就到了一个叫老庄的壑岘口。站在这里,远远地,可以看见山村。四周的山,从六盘山展了过来,手指一样蜷起,将山村拢进手心,百般呵护似的。树木笼罩着山村,阳光的影子一晃,山村绿得透明。我一眼就能找见一座院落及门前黄牛的影子,那是我的家。
走的路多,是一个人一生的资本。在山村,许多上了岁数的老人,对不沉稳的年轻人,可以在任何场合,用不屑的语气进行批评:“年轻人啊,我走过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哩。”语气平缓,却有力量。老人并不是说他走过的桥多,而是强调他走过的路太多、太长,你不佩服就没有道理。山村的路,遍布沟沟洼洼,散射各个方向,通往山村内外。多少年了,他们用脚步重复着这些道路(或者就不是道路),路也就变得顺畅,日子也就瓷实。父亲曾说,他年轻的时候,经常随长辈到山外去,购买盐、铧等生活和生产资料。天还没有亮,顶着星光出发,背着月亮回来,来来去去几百里,全靠双脚。一群头戴草帽,脚踏布鞋的乡亲,推着手推车,流着汗水,踢踢踏踏走在山道间,是一幅岁月流金的画。
换句话说,山村是道路的汇集之所。
一些主道,一些主道衍生的分支,都会在山村里碰头,很像一些亲戚,辈分明了,细究却关系复杂。山村的道路跟掌纹一样,主脉分明,那些小道,互相交错,伸向山村的任何地方,包括每家每户的院落前。我想起,电脑端口的那个标志,极像山村的主道。三条土路,铺了砂石,由南向北,最后在村北集合。或者,从北山跑下来的主道,在村北口散开,各自射向东南、正南和西南。道路的两侧,院子撒开,远看重重叠叠,实则错落有致。我家住在东边的路旁,即便在夜静更深时,也能听见汽车、拖拉机驶过,如果在白天,就能看到飞起的尘土。有时,还能听见夜行者的脚步声,在静寂的星光下,显得匆促、沉重。因地势较高,站在门前的路上,基本能够看清村庄的全貌。
山村的路,和山村一样,朴素、简单,但有柳树和野草,生长在道路的两边,路就不太孤单。路本来不孤单。深春时节,柳树的嫩枝,稠密得风都透不进去,黄鹂喜欢在其中安家,不啁啾几声,谁又知道它们在哪棵树上呢。麻雀,山村的土著,一直视路旁的树为自己的地盘,为了一棵树枝,互相争吵不休。在路边,谁家的鸡,都可以自由散步,寻找青草里的虫子。一只猫,学着羊的样子,咀嚼一根嫩草,一点不会让人觉得奇怪。村里的路,村里的人更加留恋,孩子们,三五个挤成一团,有时看草尖上的瓢虫,兴趣在于它惊慌失措时,善于装死;有时看蚂蚁打架,为分清哪一方的输赢,让青草染脏了衣服也不在乎。几位妇女,边做鞋帮边聊天,有时表情夸张,出现是非话,也在情理之中。当然也有男人出现在路上,他们边寒喧,边卷旱烟,说天气,谈庄稼。满圈的爸爸,话少,不爱凑热闹,但他是懂行的人,勤快的人。路上浮土,成天在阳光下暴晒,据说磷、铁的养分高,还有消毒杀菌的功效。他把浮土铲成堆,挑了回去,用来铺垫牛圈和猪圈,表现得很不一般。
山村里的路太多,我走过的太少。但是,我有必要介绍山村的一些道路,它们只是主道的分支,却与众不同。“所有的山道都通往高山之巅,它们有的陡峭,有的平缓,但都伸向山林深处的中心腹地”(玛丽·奥斯汀)。有好几条路通向北山,现在,我就是要沿着正北的一条小道,缓慢并且艰难地爬上山顶。小路是按照梯田的走势,慢慢形成的,狭窄,漫长。它左一拐,然后右一拐,再是左一拐,右一拐,一直拐到山顶。山顶之上,虽然不是庞大的山林,但柳树、杏树和桃树也是郁郁葱葱一片,把山顶上的一切隐藏了起来,和人的头发一样,漫不经心,却起到了妆扮的作用。山顶之上,我能看尽山村所有的道路,它们和人一样,都拥有自己的名字。我如果提起它们,它们肯定熟识我的脚步,以及声音。
依次说吧。
长路咀。这是我以前进出村庄的主要道路。长路咀其实不长,位于村南,紧临着一条名叫流长的沟,距村中心不过几百米。它的长度,并不体现在字意上。我一直说它是村庄的“长亭”或者“灞桥”。每年春节过后,村庄的许多老人,在这里要和儿孙告别,送他们去上班、上学、打工。一年四季里,总有那么几个老人,树一样立在路头,张望着沟对面的路,希望行走的那个人影,是自己的亲人。近三十年前,我在这里走了出去时,天刚亮,母亲要坚持送我,我怀揣几颗鸡蛋,走出了母亲的视线。那年那月那日那时,我站在沟对面的路上回头,看见母亲的身影仍烙在长路咀上。多年来,我觉得它和“长亭”、“灞桥”相比,远过四十里。
羊路咀。这是一条由村庄通往北山的路。从字面上看,那只是羊只可以行走的山路。这条路以前的具体状况,我没有张口询问额头布满皱纹的长者,但我知道,它陡峭,漫长,狭窄,蛇一样从山下艰难地扭向山顶。说它窄小,有些过分,毕竟能容得下一辆架子车通行。山顶上,有我们李家的祖坟,每年清明时节,我都回家扫墓。另外,有我家的几亩梯田,夏末秋初,我和哥哥们得把码在地里的麦子拉回来。下山时,撑在车辕下的我,瘦弱的双腿发酸,汗流满面,到麦场后,好几个小时缓不过神来。好在这个季节,一定能够看到远在几十里外的姑祖母,扭着小脚,一身疲惫,却一脸欢喜,缓慢地走进村庄。她带来的一小篮杏子,甜中透着酸,在炎热的天气下,给人一缕清凉。
弯路。由村中心伸向西北,爬过山梁,扎进另一个村庄。在村庄,它当时应该是一条相当重要的交通要道,连接着西北好几个村庄,使这些村庄能够抵达乡镇集市。路并不是七拐八弯,叫他“弯路”,很有些哲学的味道。我曾为此想过好久,但没有结果,只认为乡亲们就是最朴素的哲学家。这里有成百亩苜蓿地,苜蓿开花时,整个弯路都是紫色的,整个空气都是香喷喷的。我们可以在地里捉蚂蚱。有时,我能看到路上的行人走过,其中就有我家的亲戚,我就知道他们返回时,因为疲乏,一定要在我家歇息一两个小时,母亲也一定会用最好的吃喝,款待他们。
大路。大路在村庄西边,从西边的山腰通过。大路不大,两三步宽的样子。这条路实在与村庄没有关系,肯定是为了方便别村人通行,才开了这条路,“大路朝天,各自一端”,可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大路,也就有了公路的意思。“走大路的”,与村庄不相干,与村庄的人也不相干,只是他走他的大路。在大路行走的,有男有女,站在村庄就能看见。娃娃伙儿们约好了,扯着嗓子齐声喊:“大路上走着个穿蓝的,肯定是个当官的;大路上走着个穿着新的,肯定是个相亲的。”有时孩子们模仿花儿调:“大路上走着个尕妹子,把你的脸蛋儿转过来。”所以,走大路的人走得飞快,娃娃伙儿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些路,摆了多少年啊,走了多少年啊。
前些天回家,选择的仍是县乡公路,但没有像以前一样,从长路咀走进山村。长路咀太绕,得绕过两条沟,绕过三个村庄,然后进入村南。山村又开辟了新路,班车不再在一个叫店子的集镇停靠,然后步行。车是直接驶过壑岘,从沟里下去,再上来,由一条宽阔的土路,把人送到山村的西端。
那些老路依旧,行走的人还是不少,隐含的风情和亲情还在。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条新开的道路,便捷、省时,山村很需要它。这条路,人们一走又该是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