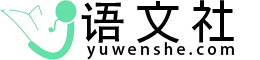敦煌一日小记散文
敦煌古称沙洲。

河西走廊最富盛名的城市,我也只是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的游客,只用一整夜穿过戈壁荒滩去敦煌,我也是生在西北戈壁上的西北人。
清晨到敦煌,最早看到就是火车站设计为莫高窟的屋檐与黄土模样,莫高窟是敦煌最诱人的名片,飞天和反弹琵琶的仙子形象理所当然作为雕塑在敦煌市中心,显然这是它们的文化自豪。
莫高窟文化代表敦煌,去敦煌就必去莫高窟。
抵达莫高窟的时候几乎是最恼人的正午,烈日炎炎仿佛窒息,温度在戈壁和天空之间不断反射加强,人群夹在中间炙烤,所以衣衫紧紧包裹自己,只裸露出一双眼睛观察。
应当是佛教圣地,然而崇尚佛教的人却不必非执着莫高窟,石窟里的功德箱或许空空,那里我见到的学者打扮的人远多于僧人,莫高窟的价值贡献岂至于一个宗教。
佛学在汉朝因皇帝的一个梦传入中原,马上中原文化的雄厚底蕴下汉传佛教自成体系,至于在莫高窟中的壁画雕塑艺术中,它自身的历史风土人情研究价值远远超越宗教意义,佛道文化和谐共存,两教的神明雕塑并肩站在一起。中原文化和为贵的魔力。宗教信仰差异造成战争流血种种,唯独在中原文化里它们并肩,以西方文化里的天使为原型的飞天以中国画的形象,被画在佛教故事中。没有人强制绝对同化,然而日久天长各方习俗都被拿来融合成一个,用在一处,古时汉人就有天朝自信的气度。
有信仰的人可能内心踏实,然而我以为不匍匐于神明的自由更加让人渴望,当然这些不妨碍我尊重并欣赏宗教艺术,反而因为不必畏惧所以能正视神明,我可以用欣赏艺术的角度无微不至地观察。
艺术品总在时间的滚动下留下蹩脚的遗憾,窟内深处高远处的壁画与近光处的色调已经截然不同,长期暴露在外已经使得它们氧化变色,从原来鲜艳的颜色日久变成灰黑或者褐色,人像的面目一片乌色,只有身上用金色染料涂抹的首饰冠带还有闪亮的金色。视之如珍宝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惊慌失措地守护着最后的颜色,我只能凭借斑驳古迹现如今的模样,竭力想象从前工匠笔下一笔一划描摹的秀骨清相的眉眼身形,一锤一凿刻画的衣带当风,色彩是盛唐的博大面貌,然而盛唐风貌已经是古卷里的尘土墨迹,壁画文物又不能磨洗加彩,前朝于是就让它坠入历史洪流吧,世人已经不再深情追思它了。
离开莫高窟的时候戈壁上的太阳依旧毒辣,炎炎烈日,皮肤竟然会伤于这样摸不到的金黄色日光,莫高窟以外有几棵古老的白杨树,树干皲裂,这样四面沙地的地方只有他们和那些顽强对抗自然的人群才生生不息,但是那两三人才合抱的树立在干褐色的莫高窟遗址之前,怎样都是荒凉的。
四面是不毛的荒地,人为拉起的电缆线都寥寥,山在更远处。
再远是遥望的玉门关。
敦煌另一处景是鸣沙山月牙泉,距离莫高窟不远,公交车直达,整座敦煌市凡是有机会的地方必要播放音乐《月牙泉》。未去之前我幻想是深深大漠里一抹飘渺的水,骤然出现在沙中的奇迹。
但是我忘记有水即有生命,甚至还没见到月牙泉时附近的沙漠里已然有丛生的矮草。
我看到棕色白色星星点点的驼队。
鸣沙山月牙泉。
鸣沙山无声。
我只听到骆驼鼻孔里粗重的喘息,驼铃丁零摇晃。所有同行者都相距一整个高大的骆驼,所以没有人声,况且沙漠辽阔声音散失,然后周遭宁静。
偶尔有风卷沙刮擦衣裳的声音,风里没有沙声。
或许听沙需要更加寂寂的环境,方圆几十里无人,要沙漠里的旅人追着虚幻的蜃楼跪在月牙泉边捧起一捧沙中清冽的泉水,跪在沙地上沾湿干裂的嘴唇,尔后耳边才伴着低声的呜咽。
更加多的说法倾向于沙鸣本来就是一个传说。大概他们和我一样,格外不能说服自己这样无边无际的沙漠的言语能被人类这样的渺小小猴子靠两片薄薄声带给压抑掩盖,于是暗自劝解自己说还没有找到正确聆听的途径。
我不禁想象起千年前的骆驼是否也鼻音沙哑,在过往经商的集市上哼出一口沙鸣一样的气,过往身材魁梧的西北大汉粗声吆喝,嗓音里粗犷余音也仿佛沙鸣,缠着头巾的阿拉伯商人操着音调怪异含有沙鸣的汉语,远处就是鸣沙山沉沉的哼鸣,都是沙哑的沙鸣,深处沙漠腹地,通行的唯一语言是沙的'语言,寂寂寥寥,仿佛一个独立的国度,甚至一个独立的世界。后来时间抹去了这个世界的存在,所以鸣沙山也孤独地永远哑声沉默,多么浪漫荒谬的故事。
日光下沙丘的颜色分阴阳,从沙丘的侧峰处被劈成金黄暗黑。骑着骆驼兜兜转转绕上一座山头,最后到月牙泉的路还要自己在沙地里一步一步挪行,沙里的路难走,踏一步陷入一寸,百米的距离走得摇摇晃晃如翻山越岭,甩着双臂宛如经历了长长远远的跋涉,但最后在沙中也没留下几个一拂即去的鞋印,旅行者虽然哄哄嚷嚷,但是他们的痕迹太容易被擦干净了,所以最好的旅行者都是卑微的,离去时他们必定记着风景,但是风景一定无从发现他们来过,自然之力下人为的一切都应该无影无踪。
月牙泉边的沙混着太多细粒的尘土,我放弃了帮朋友带一瓶鸣沙山的沙的计划,死水边的沙不比活水冲刷下的沙粒干净绵顺,如果非要赤脚踩上或者装在瓶中,我宁愿选择黄河边沙坡头的橙黄沙砾,这里毕竟是戈壁荒凉。黄土地绵细干巴巴没有养分,风扬起它就变成漫天灰尘,混在沙漠中就是灰蒙蒙的沙,混在月牙泉边的水草下就是稀烂的泥。西北人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皆是这样的光景,倚着祁连山的狭长地域,永远土地干瘪,此地没有春风,离别也难为一首折柳曲。但也是这样的黄土筑长城万里,或者是从这样黄土中生长出来甜冽的葡萄,从这样的黄土中掘一块夜光杯的玉石,成了戍前战士或者贬谪塞外诗人的杯中愁,酒精幻化成亦虚亦实的东西,聊以泄恨聊以解怀,这种文人意趣在这里自成一派。
月牙泉是沙漠中突显的一弯碧水清泉,有首柔美的歌唱它,想啊盼啊月牙泉。月牙泉边听不到鸣沙大概有这首歌一半功劳,音箱里婉转的声音透过嘈杂人声甚至都还清晰可见。千年前百年前月牙泉或许救过太多途经行者的命,多少行者想啊盼啊的一弯水。古人拜谒鬼神,倾尽千金万金用在开凿石窟上积攒功德,但其实不如拜一拜这弯清泉,它才是慈悲为怀救人于死亡边缘的神明。或许信徒只认同是自己的祈祷让神明带给他起死回生的机会,然而科学事实是水源才能救他的命。泉水如今算是失落了,污浊混沌,游人也不必执着喝下这样的水,路边商贩兜售各种的饮料,况且月牙泉如今被一圈月牙形状的木栏圈起来,水边丛生芦苇,伸手不可及。生在水乡的南方人看了可能嗤笑,西北人却要敬畏地鞠躬拜它的神奇。
大漠日落应当凄美,然而日落后即便是盛夏也会有冬日寒凉刺骨,我没有等到落日,我毕竟不是西出阳关的孤女,毕竟不会弹琵琶,也没有焦尾琴。我也许可以像一个现代浪子一样抱着吉他唱几首古旧的民谣歌曲,可我又不是流浪歌手,我只是一个庸俗地热爱黄土地的游客,不搞艺术创作的游客不该过分深情,游客应该规规矩矩在日落后返回游客中心。
日落后则要回到有人烟的地方看看灯光如昼。
市中心距离景点格外接近,或者说市中心不过是倚着景点建立起来的小聚落。敦煌并非大城市,市中心就仿佛是一个不太四方的一般街区,本地居民可能眼见我们这些防晒得小心的外地游客心有不屑,他们干干净净地走在阳光里,只有游客才会全副武装地和紫外线抗争,于是是主人还是外来者一目了然。我注意到他们多数皮肤棕褐色,尤其出租车司机脸上有酒红色的影子,身形大多魁梧,眼睛使得我想起壁画上那些西域使臣的细小眼睛。西北自古是民族复杂的地方,胡汉交融的产物是我们是河西走廊的千万居民,方言中演变出新的音调俚语,肠胃也只是依赖于这里的水土和面食。虽然是大漠里的城市,这里的街道两侧最不缺郁郁茵茵的树,街道规划整洁,城市里尽处是巨幅印有莫高窟或者飞天的广告牌,时时提醒旅人身在敦煌。穿过霓虹色的敦煌城区时会发觉多数房屋刻意建筑成仿莫高窟的外表,一律要土色的楼身和朱红色尖角的楼顶,弄巧成拙的商业行为,但如若不是这样的建筑,我也难想象敦煌还应该有什么样的城区规划,毕竟他们复制莫高窟复制得理直气壮。
沙洲夜市上集中了种种旅游纪念品,皆是有关壁画的工艺品,或者彩色沙子制成的小装饰品,或者印着风景的明信片。有的也别致有趣,但与全国各地的各式景点没多少分别,所有店家的货架上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大半产地是义乌的小摆件,游客却买回家,图一个当地风情。但这样也不妨碍我去买下几个别致的彩色小沙瓶留作纪念,旅途匆促,总该留下点回忆的信物,睹物来思念一座曾跋山涉水抵达的城市,从此那城市对于你总有不可名状的情感在其中,我们可是操控于感情的温柔生物,温柔地购下一个物件,温柔地存留关于一座城的记忆,记忆造就独一无二的人格,唯一的你自己。
第二天就应当启程离开敦煌,旅途毕竟有下一站。
戈壁依旧是戈壁,土黄色,沙漠颜色亮泽一点,金黄色,西北人全部的生命只有这些色彩,最后终有一天化身入黄土,仍然离不开这片土地,所有人对于家乡不过如此的乡土依恋。
生在西北便知大漠狂沙美过江南水乡。
作用浅浅。
最是至爱西北的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