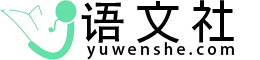我灵魂的故都散文
外出求学,颠簸的火车宿命般地穿过岩洞、引桥,颓靡的意识中也呼啸地填满往昔的缕缕回忆相思,从小学到大学,与我那生我、养我的故乡小村庄,一别竟十余载……

路
故乡是一个奇小的村庄,仅有一条水泥大道与东西毗邻的县城沟通。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水泥公路还只是一条铺得平整的泥巴小路,一遇雨天,泥泞不堪。小小的“棚车”(一种驾驶室极小,只有中等容量车厢,车厢内两边各一排长条凳的小型交通用车)发挥着公共汽车的作用,把村里村外连通。这条干道捎去了村人无数的憧憬和期盼,又带回或好或坏,有关外面世界的讯息。一条泥巴路,招摇地承载了多少个年代。
比起那贯穿村子的干道,村子里的大多小路,还只是鹅卵石、青石板铺就而成的。石缝里,墨绿的苔藓黄了又绿,一枯一荣,诉说着小道的沧桑,道着小村的历史。明明灭灭之间,又是数载。踩着这路的孩童,转瞬即成稳重的当家;蹒跚于这路上的老者,看尽人世浮华,成了明日的一钵黄土,添尽了哀思悼念。
我从这路走来,走了几年,别了又几年,恍惚梦见故乡那几条小路,愈显得狭窄了。四通八达的国道湮灭了曾经的那些旧路,模糊了我的愁思,记忆宛如泡进了苦咖啡,印象中的小路呵,已经显露出咖啡奢靡的质地,有种人造历史的虚妄和矫情,那些细碎的苔藓洗染上金铜色,多了世故和功利……
屋
小村的人家不多,上个世纪留下的土屋挺过无数风风雨雨,屹然地扎根在故乡的土地上。班驳的外墙,坑坑洼洼,朴实的土墙露出并不光滑的内里。抚手触之,历史的厚重甸得我生疼。不像现如今那些喧嚣都市里的摩天大厦,那些被指“光污染”的玻璃外墙,那些被洗涤剂每日冲洗的现代化建筑,滑溜得哪里盛放得下一点零星的历史片段?记得小时候,最爱在外婆土屋前撒娇玩耍。外墙连着一根蓝色的广播线,每到中午,和着外婆厨灶散发出的蒸汽,播着“小喇叭广播节目”和一些我并不甚懂的吴侬软语,所以中午总是在一阵童真童趣的咿呀中,吃完既定的午饭。记忆中的那条广播线,平添了深深的温馨,以至于如今回味起当时,依然有根有据、有内有容。
南方的屋子都是坐北朝南,房屋的空间虽不大,但是从中隔出一个小阁楼,却是那个年代房屋的基本格局。于是,木梯总是架在阁楼的天顶上,光滑的木梯经历了祖祖辈辈的攀缘摩擦,传到了外婆的手里,带着上个世纪的温度。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爬上了那阁楼。木梯没有想象中的摇晃惊险。或许是经过了好几代的攀爬,那姿势也就成了亘古,温顺地习惯负重,不哼一声……天顶那一方寸开口便是阁楼的出入必经之径,长年投下屋顶上亮亮的光。阁楼距房顶很低,当我渐渐从自如上下阁楼到终于得下意识猫着腰活动,天顶下望,外婆容光不再红润,那隆起的脊背,在光线的反射下,白晃晃的,晃得我几乎睁不开眼……
土屋一共有四间,算上阁楼有两层。舅舅总是戏称其为典型的三室一厅两层“小别墅”。外婆睡东厢房,舅舅一家在西厢。剩下两间,一间做厨房用,另一间则是吃饭兼会客的门厅,也是这类房子中最体面的,零散地放着一些常用的木制农具。一张八仙桌加上几张陈旧却干净的红木方凳,构成了门厅中的主要家什布局。原先还有一个木橱柜,此后被外婆的三轮车取代。勤俭持家是上一辈留下的家训。因而屋子里外,总是被外婆操持得清洁舒服。屋内最奢侈的家当就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大吊扇,据说是当年全村都轰动了。
小的时候,常常端坐在门口的门槛上,眼巴巴地看着墙隅一角的狗尾巴草,遥想未来,世界充满了惊喜和新鲜。如今,已知越来越多,未来的成分急剧被稀释——我也到了快成家的年纪。舅舅一家早几年搬进了新盖的真正两层别墅,惟独外婆伴着炊烟鸡鸣,秉承着“勤俭持家”的遗训,打点着屋里屋外,佝偻的身影被风霜打得愈见萧条。老屋子,有时承载了几代人的生命质量,事过境迁,却成了羁绊,一个不能算累赘的小小心结,一如孙犁笔下,故乡旧居的房顶上突兀地冒出的杂树,虽不茁壮,却真实地在扎根、繁衍。
春节
乡下过年和城里总是两样的。这是我搬离故乡,蜗居在城市单元格中,每每观望着天边节庆的烟火所感所想的。待在故乡小村的短短几年里,逢年过节总是一段快活的.日子。年前家家置办年货,外婆杀鸡宰猪,厨房终日热气腾腾。小姨坐在灶前忙着添柴火,毕毕剥剥的,预示着新年的新气象。五岁以前的记忆,在我胸中已经残存不多了。但是有一幕记忆犹新:大年夜的晚上,父亲搂着幼小的我,穿过外婆家的厨房。烟雾缭绕,我欣喜地听见一家人喜悦的忙碌声,至今作为一段背景乐,在这段并不清晰的记忆里衬成了隽永。春节里,迎龙灯、演社戏……这些独到节目的魅力,丝毫不亚于美国钻进烟囱的圣诞老人。我放着“大地开花”(一种烟花的名字),吃着冰糖葫芦,穿着崭新的衣裳,挤在戏台下的人群里。满眼都是五彩的戏服、夸张的高脚、精致的脸谱,满耳充斥着圆润又犀利的唱调……依偎在家人用军大衣围成的襁褓中,甜滋滋地挥霍着幸福。那段岁月,烦恼固然存在:糖葫芦怎么这么粘牙?兜里的小爆竹快没有了,外婆今晚会做什么好吃的啊……
今天看来,轻描淡写得如同掠过耳畔的一句唱词,我听不懂它,它也无暇顾及我,只是似懂非懂地图一阵子热闹。拜年、鞭炮、海吃、一群年纪相仿的小伙伴,而今重温那些在特定的年岁,在故乡旧居里度过的春节,无意识状态下联系起的字眼。如今,春节照过,只是有些美好的东西是需要年岁来支撑的,年华不再,远离故乡,这个支柱也如同灌满了碳的生铁,弹指易碎。除了奋笔疾书,在文字中找些慰藉,我还能做什么呢?那大段大段的美好,分明在我眼前轰然倒塌,分飞的碎屑迷离了双眼,继而开始流泪。
活动
没上小学之前的年少日子,总有一群小伙伴和我,在那片盛满了我满腔深情的土地,跑啊、闹啊。都是少不更事的毛头小子,没事窜到人家的地里,掀起几个胡萝卜,在小溪边淘洗一番,便脆生生地咬开了;桑葚成熟的日子,采撷一筐,吃到舌头发黑,笑哈哈地互相取笑“哈,你中毒了。”又跑散开去。类似的例如在夜里捉迷藏、在纺织厂的小池子里游泳、去田间找野果鸟蛋,如此乐事,不胜枚举,与鲁迅在三味书屋的日子一样,各种童趣如覆盆子,独特哪。
村子附近有个鱼塘,鱼塘附近就是大山。翻过大山到达另一头,那是婶婶的娘家,一个盛产栗子和菱角的小镇。调皮的我们,摸鱼、偷板栗,“无恶不作”。谈笑间,挥别了旧居,挥别了栗子的味道……硬生生地扎入了“现实”之中。
趁着假期,回了趟故乡,那片天没变,那片天底下还仅存着些许我熟知的乡音,找回了一部分习惯,兜兜转转,自己毕竟不是一个陌生人,所以就心安。一幢老屋的外墙,在“建设新农村”的号召下,刷成了清一色的雪白,整齐划一。那些凹陷坑洼,也被现代涂料砌满。棱角磨平,那一大段的“历史”和回忆拌着涂料,藏匿在白色的虚掩中。村里活跃了好多外来的打工仔,青石小路上,迎面走过的多是生面孔,带着生活的艰辛和充实,冷漠地擦肩而过。趴在小路一边的古井上,仍是那熟悉的澄明得倒映出人影的井水和水滴千尺的空旷回响,可惜影中人不再,不在了。
外婆一个人硬是不肯搬进舅舅家的别墅,孤零零地住在原先容纳一大家子的老土屋,维系着彼此的生死,兴许是在守望,守望着一座叫作“怀旧”的城池,守望着一份单纯不变的乡情。
[后记]
如果传说中的灵魂确有21克的重量,那么今天我结结实实地掂到了乡愁的重量,她焕发着种种令我怀想的美,念及的好。让我用一颗脆弱的心去负重,沉甸甸的,却真实。告别旧居时,窗外纷扰的漫天黄叶,落成一个个新坟,埋葬了往昔。怀念故乡的老屋,怀念屋中的外婆,和那一段与之匹配的年少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