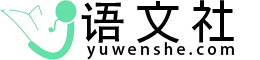说话的方式散文
对于写作者而言,写什么固然重要,怎么写好象尤其重要。对前人作品的回顾,还没怎么说到内容,总是先说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派。就像是江湖上的武术派别,门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不管怎么样讲,写作总是一件手艺活儿,它讲究套路和风格。它是另一种说话的方法——诚如周作人所言,是“风干的谈话”。既然是谈话,就要有谈话的艺术,或者叫“说功”,其实它的艺术旨趣恰恰是在这里。像相声一样,我们喜欢老派人说的相声,如侯宝林,马三立,他们完全是靠“说”来解决问题的,不动声色,暗藏玄机,包袱抖开让你喜不自禁。不像现在那些说相声的,什么都整到舞台上去了,看见观众不笑,恨不得躺地上跟你打滚。现在有的写作者也是如此,说到尽情处,怎一个“脱”字了得!眼见着要把一个文坛变成声色场。

极度发达的物质社会和我们不断膨胀的需求欲望正在勾肩搭背相互调情,这是我们所驱使的现代化迈进的一个新门槛。文学在物质化的世界里正在渐渐失宠,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去我们曾经用文学点燃生活;那么现在,如果说生活是一只炮仗的话,我们的欲望就是一盒干燥的火柴,而文学只是爆响后沉默的灰烬。但是,虽然文学已经沦落到如此,但他绝对不会消失到无,更不能忽略不计——热爱文学就是热爱善和希望。一个失去文学的世界,将会变得惨不忍睹——首先我要申明的是,我竭力为文学和那些皓首穷经的作家们声辩,所捍卫的并不是一个艺术门类和消遣的途径,而是对这个世界深邃的渴望和热爱。
作家的道义和责任感,有时候也反映在说话的方式上,使作家的生活态度在作品里显影。像十九世纪以来的俄罗斯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他们彪炳千秋的作品,尽管大多数述说的都是苦难,但我们从苦难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更多的对生活的悲悯和对生命的热爱。崇高的悲剧美、对人性不竭地追寻、对苦难宽容的态度,是俄罗斯文学的最伟大之处。他们虽然没有对个人的磨难置之不理,但绝对没有狭隘的谩骂和咬牙切齿的嫉恨。在作品所反映的个人的苦难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悲愤,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雪,刮过的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苍凉而又博大,而又有凛然的尊严,而又有深长的意味。而我们的一些作家,还没开始说话,就先被自己激动得不能自持,话一出口,就变成了一支支粘满毒液和唾液的利箭,漫无目的地横飞。他们被自己的情绪牵着走,悲愤和不平都是一己的,和别人几乎没有关联。对于苦难,他们好象理解成就是悲哀。他们的姿态比苦难本身还低,他们被苦难压迫着,根本无法超越它。他们靠描摹苦难的细节煽情。这不能显示他们的悲悯,充其量只是可怜,因为真正的悲悯是要有足够的尊严的——不管是悲悯者本人还是被关注的人;而且它是通过微笑来表达的,而不是咬牙切齿。而他们只会躺在自己的伤口里呻吟,把个人的痛苦看得高于一切,哪怕是隐私,也被涂上了艺术的光环。他们靠自己的痛苦赚取市场和同情。如果是写社会的不平,肯定是“洪洞县里没好人”,高高在上的官僚一律该斩,生活在底层的全是圣洁的天使——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象征。人在他们的作品里泯灭了,只有欲望、痛苦、邪恶和呻吟在那里脱窍而出,像一片片漂浮的磷火,模糊而又遥不可及。
二
俄罗斯的文学泰斗托尔斯泰,一生所探索的都是如何解脱人类的苦难,孜孜追寻人生的真谛。他被尊奉为“人类的良心”。他的作品首先改变了传统的述说方式,有时候他会义正词严地站出来,公开他的道德宣言,对作品里面的人物指手画脚。这奋不顾身像一样的献身精神,被那些学院派的评论家所讥笑,指责他是“天才的外行”。这不但无损于他的光辉,而且一百多年来时间的裁判更说明了他的伟大——因为他热爱的,永远是劳动者和弱者,是善良的人。他述说的总是苦难和社会的不公,但是除了设身处地的怜悯和同情,没有置身事外的怨怼和骂街式的暴跳如雷。饱经磨难、忧心忡忡的俄罗斯,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在他的.笔下,被浇灌成了一片充满生命力的森林和一株株傲岸的白桦树,在苦难里锤炼了信念,在打击面前挺住了尊严。惟其热爱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会进而热爱整个世界。也因为对整个世界的爱,才赢得了世界对他的尊崇。他倡导的“勿以暴力抗恶”,虽然为那些所谓的革命家所不齿,但是历史和实践证明了他的正确——饱经战乱,民不聊生,一个动荡的国度,遭殃的永远是那些手无寸铁的贫民百姓。他不是孵生一时一事斤斤计较的理性,而是永恒的道义,是言行一致的人格力量,是与那些他所热爱的人们同命运的博爱精神。正如一个后来者所评价的那样,“有的作家只给了我们一条明亮的道路。而他给我们的却是整个原野——有纵横的阡陌,不息的河流,巍峨的高山,和手足般的人们。”
另外一个被指责为不懂自己手艺的“天才的外行”是与托尔斯泰齐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先哲般的思想、夸张的热情和手术刀式的批驳,让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提心吊胆,就像穿行在阴森森的地狱里,几乎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他是敏感的,偏执的,透着热情和悲愤的道德审判官。“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景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他用另一种方式爱着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他为他们打开道义忏悔室的门,让他们面对自己的心灵——只有看到自己的丑恶,才会是善行的开始。他喷涌的热情和冷静的思索,形成了作品跌宕的旋律,让我们因沉淀的太久而已经麻木的情感得到彻底的清洗。他一泻千里、泥沙俱下的叙述好象是直奔着黑暗、愚昧和压迫而来,而蕴涵的却是无尽的悲悯和热爱,也许还有忍从。他把俄罗斯民族的善良和残酷刻画的淋漓尽致——这是个矛盾的民族,是个矛盾的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好象都不会被改变。
屠格涅夫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也是俄罗斯最懂得小说“经济和建造术”的作家。他的叙述方式既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恢宏,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深邃。他是沉着的、冷静的和隐忍的。他用思想取代了情绪,用描写取代了陈述。他和被叙述者拉开了一段距离,远远地看着他们,然后对他们的作为画龙点睛地做一些概括。他不愿意多说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不想多,那是贵族式的简洁和果断。他和托尔斯泰一样,并不是一个饱经苦难的人。但优越的生活条件,不但没有使他失去爱和思想——同情和思想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来自于富贵啊!他的悲哀既浸染着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也沉淀着一个善良的作家的艺术良知。他好象比任何人都关注普罗大众,但他的作品不是写给他们看的。他是写给他们以外的人看的,比如贵族,但一定是和他一样具有良知的贵族;比如那些闲适的人——他不动声色地告诉他们事情的,然后让他们慢慢地感动,让他们知道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和不做些什么。有一个时期,他的声望甚至超过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这既因为他说了什么,也更因为他怎么说。
三
其实有时候,文学比哲学的罗嗦事还多,它至少比哲学更不规范。所以这激起了很多人的发言欲望。既然文学是人学,那么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可真正对文学发言的人,又有很多是不懂文学,不爱文学或者是根本不看文学的。“某某的层次太低,我从来不看他的作品”,这虽然并不是光鲜的武器,但杀伤力却极大,往往成了这些人结束战斗的利器。而且,写作这种很通俗的手艺,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如果再加上网络和因话语权扩大化而造成的冲击,文学真的被熬成一锅“坚硬的稀粥”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写作变成了“个人的事情”。私欲在文字里袒胸露背,呻吟被当作了抒情,伟大、崇高和悲悯被贬做了俗套。进入文学越来越容易了,而离心灵却越来越远了——尽管是絮叨的自己的心灵,但那只是一个器官而已,并不具备思想的功能。
如同用身体写作一样,网络写作也以前所未有霸权方式与传统文学争夺越来越疲惫和麻木的读者。他们在一点上是共通的,靠传统的叙事方式无论如何也占不了上风。他们更懂得市场,知道这个以快餐文化盛行的文明古国正像一个急于摆脱农村身份的乡下人,只要是能表明城市化和现代的东西,哪怕是核废料,都会让他们如获至宝。因此他们联手制造了这次“宫廷政变”。真正的作家让出了自己的领地,要么沉默,要么卖身投靠到这场新的“平神”和“造神”运动中去——他们也急于证明,自己并不是落在时代后面的满身泥点子的阿乡。在他们的作品里,生活被一些琐碎的细节和大段大段的“思想"(有的只是刚刚被泊来的口号)所堆砌,他们用后现代的东西演绎出了新的假大空。如果一部作品,没有了对人类的关注和对生活的热爱,无论到何时,无论到何地,都不会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
渐渐平复的心灵,虽然不会再有盲目的激情,理性使我们在生活里更真实了。但仍然有人会刻苦地写作——有人是为了生活,有人是为了爱生活,有人是为了诅咒生活。写作成了最安全的话语方式,也成了最世俗的方式。我不记得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西方伟大的经典的人,怎么可以妄称是受过教育呢?”这句来自上个世纪的文化箴言,是否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墓志铭呢?对于每一个作者和读者而言,首先要读的,不是伟大的著作,而是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