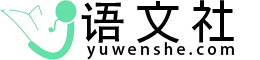春六帖散文
立春

“春打六九头”,寒气渐收,是有春始的意思了。
记忆中,有许多个立春立在腊月里。母亲蹲在门后的长宁河边洗被子,洗的是过年被子,洗过,年就要盛装而来,我们小孩子无日不激动。母亲起身将凤凰牡丹的被面撒网一般铺开,铺在河面上漂洗,顺便问大妈:大姐,打春了吧?
牡丹凤凰的红被面浸了水,颜色越发灼灼鲜艳,让人看见方方的一片喜气,载浮载沉地在水上荡漾。
其实,母亲猜到已经打春了。我想,她一定从河水的软和温里,从拂面的河风里,意会到了春气。
但到底还是立春,还只是一个开始,春色还在孕育中。长宁河边的榆树林依旧疏影横斜,一片墨色,在向晚的日光里摇曳,一副闺中人倚楼思远的寂然模样。
热闹的是村落间,杀过年猪,起鱼塘,蒸年糕……丰衣足食地来迎接农历年。
雨水
南门的护城河边,邂逅一树盛开的白玉兰。
没有叶子,只一树的花寂静又辉煌地开,路过时劈面一惊。白玉兰开在早春的风日里,很像欧洲教堂里的烛光点燃,里面举行婚礼,有一种静穆的华丽。
城里不知季节变换,但花知。
中午陪老父亲闲聊,忽然,他说,昨天是雨水。说过他一笑,我也一笑。说的时候,天正下着雨。
老父亲已经多年不事农桑,可是依然时时记得与农事贴近的节气。这是中国老式农民,他们曾经像脚踩田埂一样稳稳地踩着节气,育种,插栽,耕耘,收获。慢慢,节气成了他们一辈子行走的坐标。
我是父亲的庄稼里一颗发生了点变异的种子,正努力回归。我的雨水不是坐标,而是一间静静的书房。
那些从前的早春,下雨的天气总像是翻了又翻的不变的画面:母亲和伯母,还有婶婶,坐在堂屋里抹骨牌。天光阴暗,桌子被端到大门口,斜着放,桌角正对着大门,借着天光抹骨牌。一牌又一牌,有人和了,有人唏嘘,然后洗牌又抹牌打牌,又和了,又唏嘘。雨在门外绵绵渺渺地下,囚得人哪也不去,只待在屋子里。世界这么小,只有我和这一桌抹骨牌的中年女人们。我躺在床上看书,透过半开的房门门缝,看着她们打牌,听着她们窃笑和叹气,好像那是我读的另一本书。于是觉得,雨水罩下的这个小世界,也不过是一个书房而已。人物从书里侧身而出,撑伞一般撑开血肉的'身体,在潮湿的空气里,在暗淡的天光下,悄悄地活动。天一晴,全都消隐,变成妈妈,变成村妇,变成农民,变成很忙的人。
雨还在下,我和父亲都默然在看路上匆忙的行人,他们在招手拦车,赶着去拜年。我们像两只牛,在记忆里反刍各自的雨水,眼前的雨水似乎是别人的。
我眷念雨水之下的旧时风物,那种温润的旧意,让人觉得妥帖。
惊蛰
惊蛰总要打点雷才成气候。但是,这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天是习惯性早产,健康早产。
惊蛰前一周,雷声就在墨黑的苍穹里轰轰响起来,很有些高亢雄浑的意味。我靠在床边,睡思昏沉中,凛然一惊,想来那些懒睡在地下的昆虫门一定惊慌得不像样。
想象一下,蚂蚁,甲壳虫,野蜜蜂,蝴蝶……它们一定大呼小叫着,有的抓壳,有的抓翅膀,有的抓触角,有的抓腿脚,穿啊套啊,起床出土。一路上心里还砰砰:要迟了!要迟了!“轰——”又一阵雷声从天空滚到地底。就像我当年上学迟到,远远听到学校的上课铃声惊悚响起,眼前浮现一万张语文老师板结冰冷的面孔,“站黑板!”“轰——”心底一阵雷。
终于出土长大了,再也不用上学了,再也不用担心睡觉睡过头站黑板了。
现在,我常常充当春雷阵阵,每天清晨去轰醒我那蛰伏在被卧里的儿子。
有一天,儿子嬉笑着说:妈妈,读书太累了,做人太累了,我不如出家做和尚吧?
我说:好啊,从明天起,你是小和尚,我是师太,咱们都出家,庙就是咱家。
第二天早晨,天色微明,师太起床弄好无荤的早餐,然后锅铲敲门:小和尚,小和尚,快起来用斋,然后去念经!
春分
到了春分时节,面对春光就生了忧念。好像养了女儿的人家,眼看她快到了十七八,心里千万遍默念:慢些啊,慢些啊,一快,女儿就是人家的人了呀!
是啊,慢些啊!慢些啊!
风你慢慢地吹,花你慢慢地开,叶子你慢慢地长,小蜜蜂你慢慢地飞来……一快,春天就没了。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了呀。
晚上散步去植物园,一路春风,柔情蜜意。植物园多的是柳,朦胧的路灯光里,看见柳线垂垂,摇漾在水边。细看去,那柳早不是我雨水之后所见的窈窕的柳了,而是已经出嫁的柳,儿女缤纷绕膝。
还记得当年村子里有一人善制柳叶茶。春天,柳树爆芽,他挎了篮子去河边田头捋柳芽,回去焙茶。用稻草烧火,在铁锅里焙。后来,村子里有许多女人也跟着他捋柳芽,还请他做师傅来家里焙茶,于是一个春天,家家都有了一铁筒的柳叶茶。闻起来清香缭绕,泡在杯子里好像热带雨林,只是吃起来清苦。
柳到了春分时节,已经做不了茶了。叶子繁茂,它有了母性。
清明
桃花开到垂死挣扎一般艳烈。
在无为,在春天,必要到太平去看趟桃花,才算得是完整地度过一个春天。
桃花林的对面是一片公墓,于是许多人在清明前后就同时做了两件事:扫墓,踏青赏花。
墓地和花林,像是生命的两极。
扫墓的时候,想念先人,哀感生命须臾,可是忽然一转身:瞧,桃花正开着呢!
人在桃花丛中走,浮花浪蕊落满头,痴痴以为好景天长地久,一转身,看到了墓地,才知道长久的是寂静。花开应如梦。
我是午后去看桃花,单是为了花。一路上只想着花,便觉得自己痴情。
桃花开在山坡上,一片一片,一坡一坡,比水墨画里的桃花要务实得多。
我站在盛大的花海对面,无端忧戚。这样盛大的春色,这样浓烈的开放,捧给谁,谁能端得住端得稳?
没有谁。
当一种生命足够粗壮、一种心灵足够壮阔的时候,也许它同时也就失去了能接应它的另一方。所以,它的命运就是自己盛开,自己凋落,雌雄同体,独自芬芳。
雌雄同体的生命,一定丰盈又孤独。
桃花好像是雌雄同株的吧。
谷雨
谷雨前后看牡丹。牡丹是银屏的千年牡丹,长在悬崖绝壁上,白色。银屏周边的老百姓,像我父亲那样的老农民,习惯数牡丹的朵数来预测一年的雨水多寡。悬崖绝壁上的这丛千年白牡丹,每年花开数目不一样,据说花多那年就发水,花少那年就干旱。
我站在悬崖下,举着望远镜看那丛白花,忽然想起武侠小说里的李莫愁。那么美,那么处境孤绝,拒人千里,真是高冷的传奇。
悬崖之下的江北大地,丘陵和平原,雨水下过,土膏松软,种子窝睡在泥土里一日日发胖,生出胚芽。萌生,长叶,开花,结实,演绎热热闹闹的一生。
我在谷雨前就下了种,种了一畦毛豆,只等豆苗出土。
红尘之洼,种的是生死荣枯、烟火庸常。无传奇。